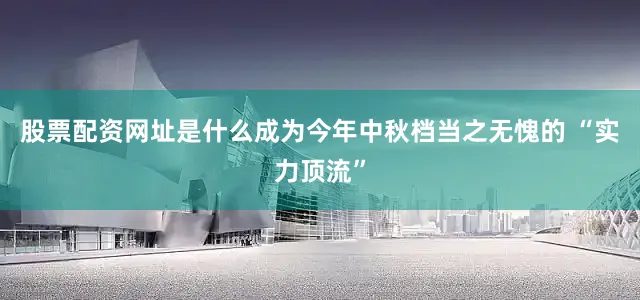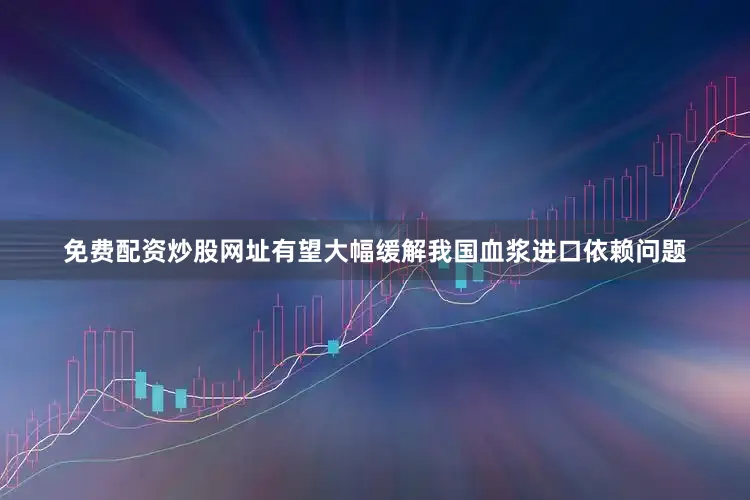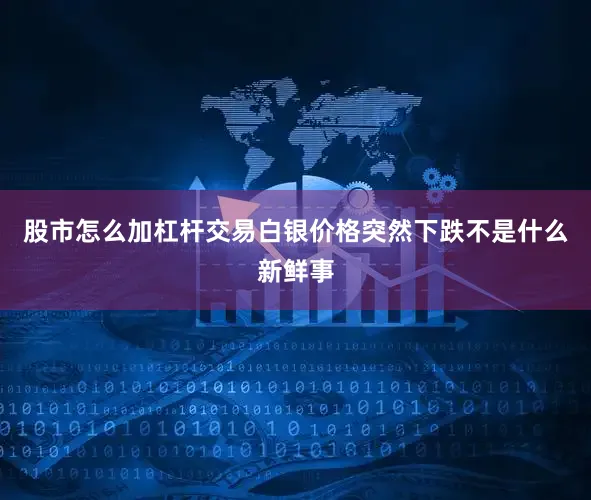10月19日,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门口排起了等待观展的长队,许多上海观众为了刚刚开幕的“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而来。与此同时,来自广东、上海及全国各地30多位学者、艺术家与策展人围绕“中国近现代美术与广东实践”与“广东近现代美术的区域互动与历史叙事”两大主题,进行了深度研讨。
 名家齐聚上海美术馆
名家齐聚上海美术馆
历史的互动性
广东,作为中国最早拥抱海洋文明的地域之一,漫长的海岸线不仅是地理标识,更是中外艺术交融的长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广东与上海两地艺术在百年前已有深厚的缘分。我们耳熟能详的海派画家林风眠、关良、陈抱一等都是广东人,中国美协理论与策展委员会主任尚辉谈到两地的共同性时说:“中国现代美术的发生既是中国迈进现代社会而自我变革的必然,也是积极引鉴西方美术为我所用的结果。”尚辉表示,“这次展览中,很多作品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美术史上的经典名作,若没有这些经典名作,中国美术史有一半是缺失的。尤其是1949年前,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为代表的岭南画派画家,在上海的6年时间,深刻地影响了海派美术的发展。上海与广州作为中国开得最早的通商口岸,在建立现代城市的过程中均曾得益于口岸文化的开放性,从而形成了这两地的互动与对中国现代美术的共同缔造。”

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岭南画派纪念馆馆长李劲堃表示,广东美术百年大展是馆藏作品作为区域美术重要的一个抓手。“这次我们借了上海部分的关良、林风眠的作品,这种在地的互补,无疑大大丰富了广东人在各地的发展。同时通过整体的回溯,对广东在未来如何前行,也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毛时安把这次在上海美术馆举行的广东美术百年大展比作“海派文化和岭南文化、岭南画派和上海画派的一次深情热恋”,他希望这次热恋能够开花结果,“要结婚,还要生孩子,还要繁衍后代,让我们两个画派能够为中国美术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广东的推动力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林蓝等多位与会专家都提到了展览中的一个环节“抗战木刻”,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吸引了一批年轻版画家围绕在他身边,以木刻为武器,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唤醒民众意识。在与鲁迅直接交往的木刻青年中,粤籍艺术家占58%,就连鲁迅本人亦曾说:“擅长木刻的,广东较多。”比较著名的木刻家有黄新波、陈烟桥、李桦、罗清桢等人,李桦还于1934年在广州发起组织“现代版画会”以响应鲁迅的新兴木刻运动,使广州成为南方的新兴木刻运动中心。
林蓝尤其提到广东的“真金白银”对于艺术的推动,1912年,高剑父四兄弟拿了广东省革命政府的10万元大洋来到上海创办《真相画报》,将岭南画派的革新思想与上海的国际化视野深度结合,不仅刊发黄宾虹吴昌硕等海派名家作品,更是首次系统引介世界美术潮流,成为连接南北艺术的桥梁,为中国画的现代化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高剑父还对年仅17岁的徐悲鸿青眼有加,主动提出高价收购徐悲鸿的作品,“真金白银”地从实质上“改善青年艺术家的生活”。
现代的创新性
广东美术在现当代艺术方面的观念输出对全国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中,不乏当代艺术方面的呈现。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海派艺术馆馆长李磊提到“最先发生在大湾区的实验水墨艺术,以期延续传统文脉,促进传统水墨媒介的当代转换,创造中国人自己的当代艺术。‘上海新水墨’的代表人物陈家泠、张桂铭、卢辅圣等都依托广州、深圳拓展艺术影响。历届广州三年展、深圳水墨双年展等大型国际展览都与上海密切互动,相互支持。”
上海油画雕塑院院长江梅谈到观念的输出与广东地缘艺术文化发展有关,“有能力输出,说明已经脱离了本土化,在全国的视野、全球化的视野中重新审视自身文化的创造,因为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实践才有可能谈得上输出、传播、影响外界。在国内国际艺术舞台,都能看到广东的策展人、批评家、艺术家的身影,感受到他们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百年美术发展中,中国艺术家一直在进行中西融合,上海和广东就像两条大河,时有交接,在流淌的过程中各自发展主体性,也在不断地互补,而这两条河流都是敞开的、开放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
“‘其命惟新’深刻凝练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精神,而‘折衷中西、融汇古今’则为转型指明了一条鲜明的实践路径。”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陈翔在昨日中华艺术大家说之“岭南文化名家大讲堂”中这样表示。
盛达优配-券商配资-炒股配资平台-线上配资炒股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